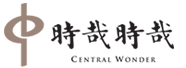- 季氏16-1
 YT
YT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: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:求,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,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,且在邦域之中矣,是社稷之臣也,何以伐為。冉有曰:夫子欲之,吾二臣者,皆不欲也。孔子曰:求,周任有言曰:「陳力就列,不能者止。」危而不持,顛而不扶,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,虎兕出於柙,龜玉毀於櫝中,是誰之過與。冉有曰:今夫顓臾,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,後世必為子孫憂。孔子曰:求,君子疾夫,舍曰欲之,而必為之辭。丘也聞,有國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,和無寡,安無傾。夫如是,故遠人不服,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,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,相夫子。遠人不服,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,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,不在顓臾,而在蕭牆之內也。
【歷史背景】
顓臾在夏時已是東方國,鳳凰為彼圖騰。商時山東地區還有宿、任、須句等方國。顓臾於西周時被重新加封,附屬於魯,為東蒙山主祭。《左傳》並未記載季氏伐顓臾,或是本章孔子勸阻之致。
季氏將要攻打魯國的附庸國顓臾。冉有、子路作季氏的家臣,來拜見孔子,報告此事。
【白話解釋】
孔子指名冉求說:求,這恐怕是你的過失吧。顓臾,是周朝以前先王所封,在東邊為蒙山的祭主,且它處在魯國的疆域中,是魯侯的社稷之臣,為什麼要去攻伐呢?
冉有推託地說:季康子想要攻伐,我們兩個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,雖然不想,但必須配合。
孔子說:冉求,古代賢人周任有句話說:輔佐別人,必須度量自己的能力,能做就做,如果不能,就應該辭去職位。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,見人摔倒不能扶起,要這種扶持人做什麼?況且你說攻伐顓臾是季氏的主張,這話就已經錯了。如同猛虎、犀牛從柵欄裡逃了出來,龜殼美玉在匣子裏毀壞了,這不是看守者的過失嗎?這就好比季氏若伐顓臾,是當家臣不諫止之責。
冉有在被孔子譴責的情況下,說出伐顓臾的理由:如今的顓臾與以前不同,城邦堅固,且與季孫的私邑費縣相近。現在不攻取,將來費地會保不住,必會給季氏子孫留下禍害。
孔子說:求,你說的這個道理,君子很厭惡。明明是季氏貪求顓臾之地,你捨之不說,而捏造一些牽強的言詞。我曾聽說,無論是有國的諸侯,或者有家的卿大夫,不必擔心財富不多,只需擔心分配不均;不必擔心人民太少,只需擔心社會上下不安。若是財富平均,便沒有貧窮,和氣則能使遠方來歸,便不會人少;相安則不會招來外患而國家不致傾危。誠能如此,如遠方的人還不歸順,則我修養文化道德,使其來歸。他們來了,就得使其安心。孔子責怪冉求之後,接著便連子路一起責備而說,如今仲由和冉求兩人輔佐季氏,顓臾乃至以外的邦國,這些遠方的人不歸服,而不能用文治教化使他們來歸,國內又由於三家把持魯君,人心分崩離析,一盤散沙,如今尚且都保不住家園,還要出兵伐國內的附庸,外患都不能守國了,對內還要自己打自己,製造內亂,同室操戈。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,卻在宮牆之內。顓臾不 是季氏所患,季氏真正所患或是家臣伺機犯上作亂,或是魯君伺機欲奪回政權。
【章旨】
此章孔子訓悔門人,誅奸人之心,抑其邪逆之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