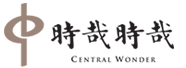- 子路13-3
 YT
YT
子路曰:衛君待子而為政,子將奚先。子曰: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: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:野哉。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,蓋闕如也。名不正,則言不順。言不順,則事不成。事不成,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,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,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,無所茍而已矣。
【歷史背景】
孔子在六十三歲時第五次入衛國,當時衛國的國君是衛出公蒯輒,已繼位四年,他想要請孔子作衛國執政大夫(宰相)。為什麼國君名號為出公呢?因為蒯輒的父親蒯聵是靈公的太子,因弒母未成,負罪逃往國外,靈公卒,由靈公的孫子輒繼位為君。後來蒯聵回國,取得君位,輒則出奔,因此稱為出公輒。
據左傳記載,蒯聵在魯定公十四年,因為不恥母親南子淫亂,涉嫌想殺南子,弒母未成,奔往宋國避難。魯哀公二年春,衛靈公有意立公子郢為太子,郢推辭。同年夏,靈公卒,但未廢蒯聵太子的身分,南子命公子郢繼位,郢再堅持,遂立蒯聵之子輒為衛君。那年六月,晉國的趙鞅助蒯聵返回衛國戚邑。魯哀公三年春,衛石曼姑等帥師圍戚。歷史學家稱他們為父子爭國。其實是否出於父子本意還是疑問。此後蒯聵一直居在戚邑。至魯哀公十五年冬,蒯聵與渾良夫等潛入衛家,挾持執政大夫孔悝,強迫與之結盟,蒯聵遂被立為國君莊公。魯哀公十六年,蒯輒出奔。
所以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,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,時在衛君出公蒯輒在位四年,想請孔子為政作執政大夫。當時孔子弟子高柴、子路等皆在衛國當官。
【白話解釋】
子路問孔子:如果衛君蒯輒等待您去執政,輔助他治國,您首先要做的是什??孔子回答:要先端正名分,因為蒯聵被晉國勢力挾持,要與兒子爭國,但他的兒子蒯輒在衛國繼位為君已經四年,國人已視他為國君,且欲抵抗晉國入侵,可是蒯聵他還是有世子的身分,也有作為國君的合法性。此時衛國的政局就是如此複雜。子路不解孔子深意,所以問孔子:有必要這樣嗎,會不會說得太遠了,而非當務之急。意即衛君蒯輒在位已久,繼續當國君即可,何必還要端正名分?孔子糾正子路說:你怎麼像鄉野村民一樣,看不懂端正名分這件事的重要呢?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,一般都採取保留意見。名分與事實不相符,則說話就不能順理成章,沒有說話的名分,要如何推動事情呢?普通事情都辦不成,還談什麼推行禮樂呢?既不能興禮樂以化民治國,自己都不能正名於上,人民犯罪又如何能施設刑罰處分呢?則刑罰沒有標準,人民感到手足無措,不知如何是好。所以君子做事,必定先正其名義,必使恰如事實,話才能順理成章的說得出來,能順理的說得出來,必能行得通,沒有立場說話,試問要如何推展事情?所以君子對於他所說的話絕不苟且,必使名正言順。
【章旨】
此章論為政在正名也。